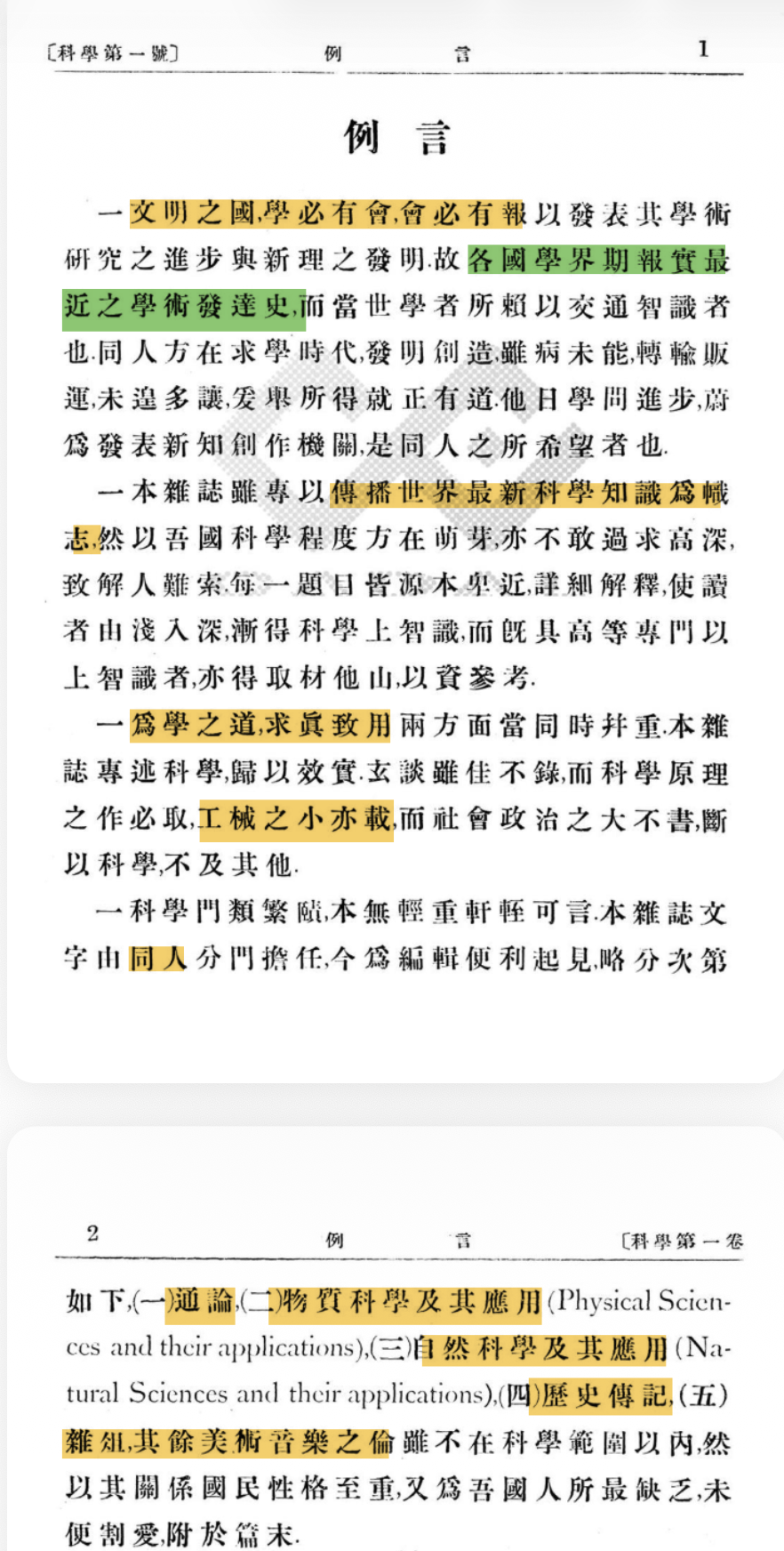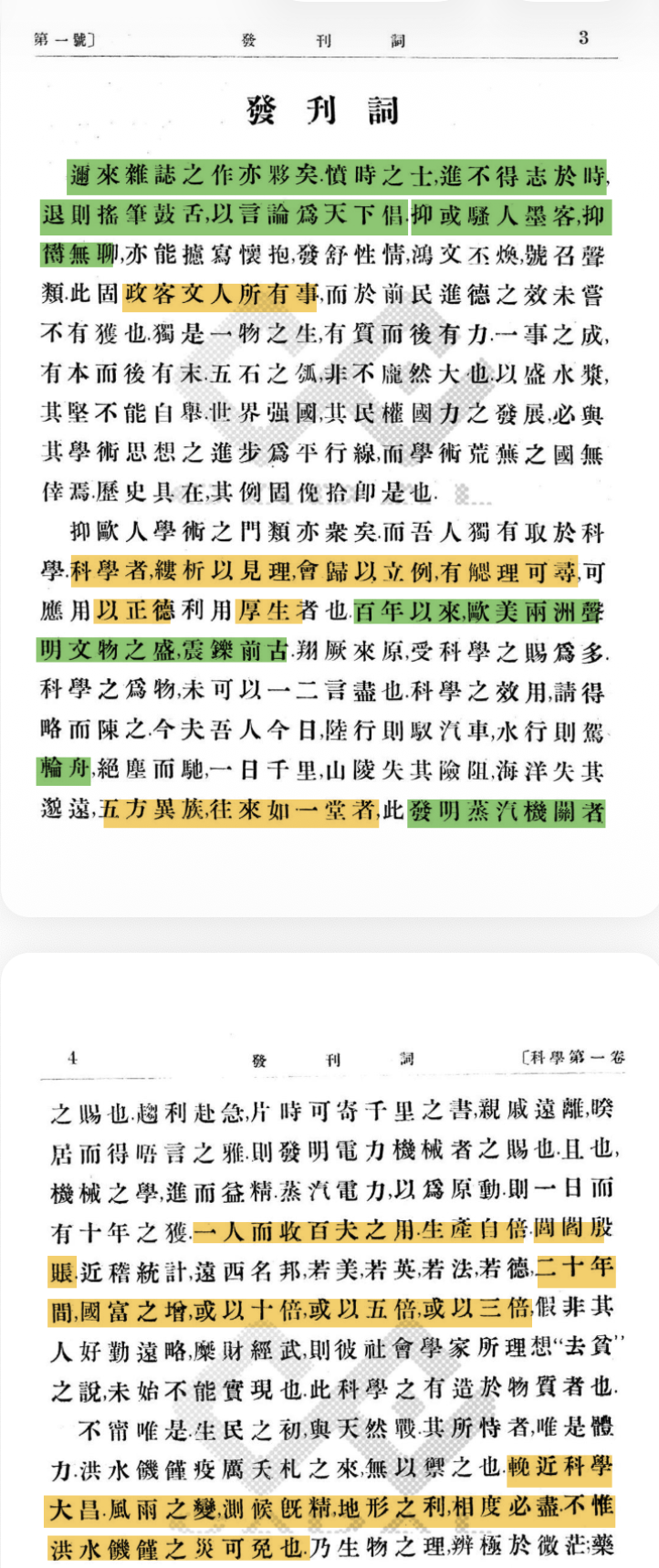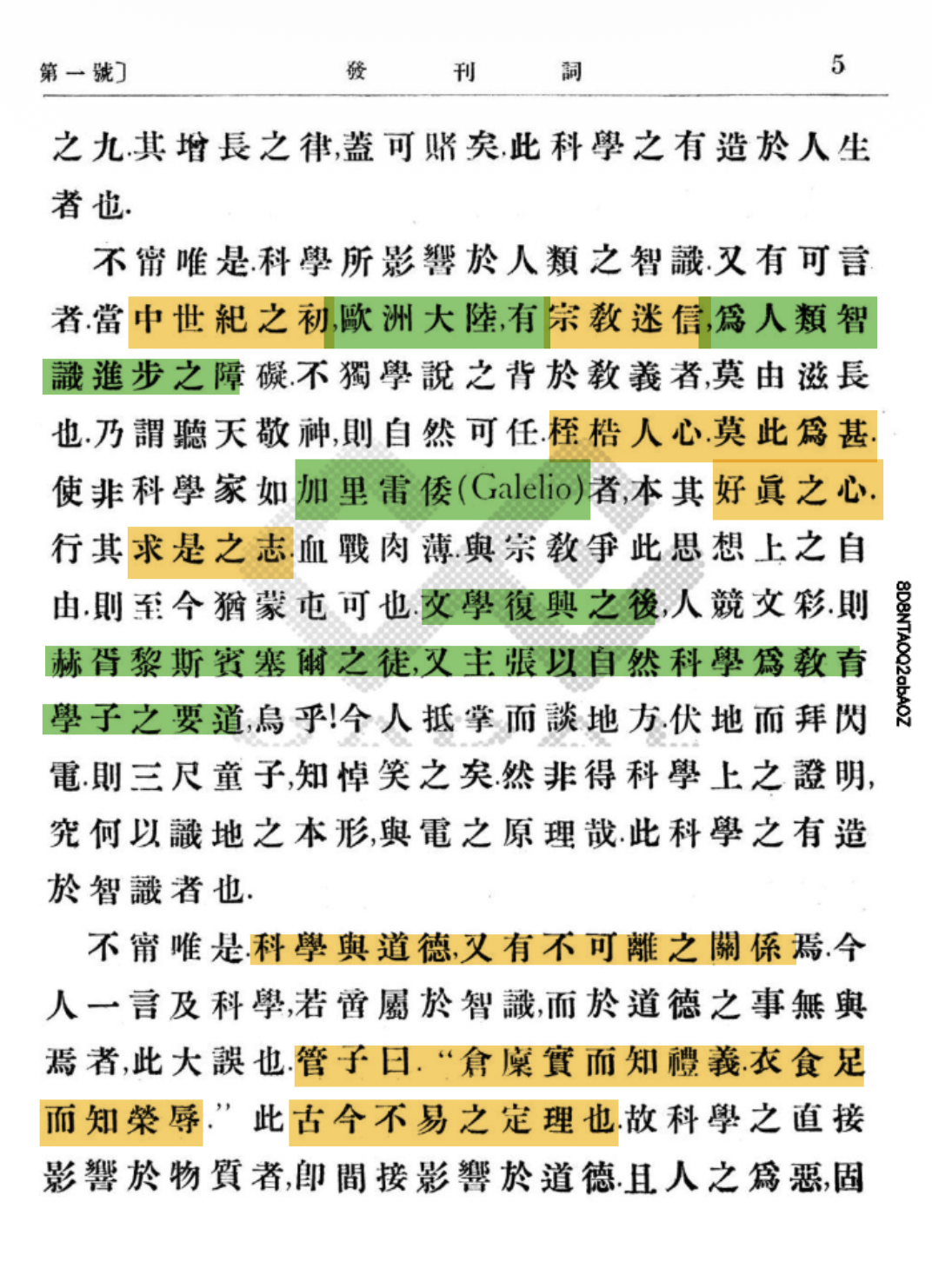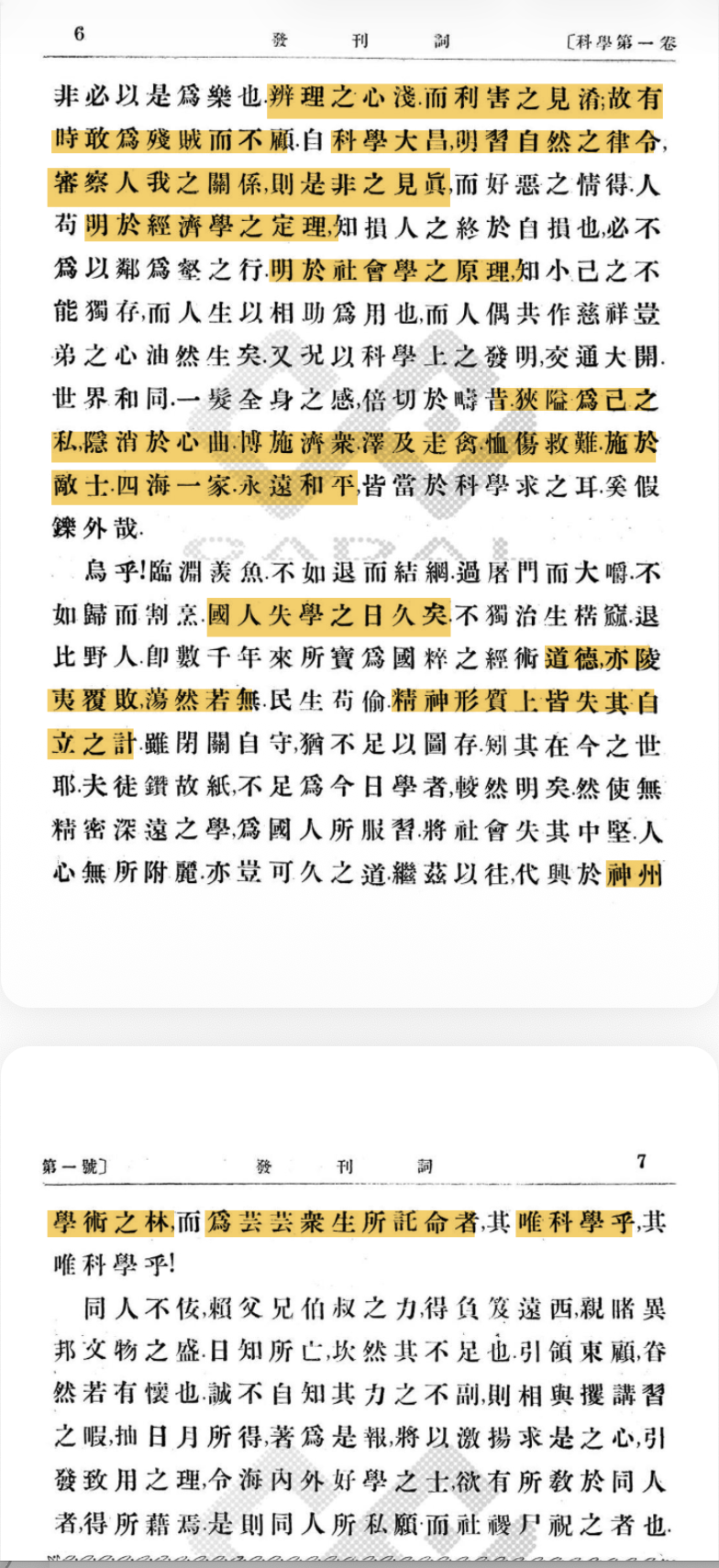科学的目的:求真、致用、正德、厚生
虽说当下是科学的时代,但是科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,却莫衷一是。如果按西方的科学历史叙事,得到的答案只有两种,一种是满足个人好奇心的探索,比如伽利略,牛顿对天文问题的好奇,以及法拉第对电磁现象,欧拉对数学问题的痴迷等等,另一种就是获得战争的优势,比如伽利略、牛顿都参与过炮弹弹道的研究,维纳的控制论则更是在二战中研制自动高射炮产生的
但是在我们考察科技的历史真相过程中,发现中国古人之所以发展科技,其目的是为了提升生产效率,降低人工劳动的疲劳和生命危险。
那么古人究竟是如何看待科学的目的的呢?
今天我们终于找到了答案。即「求真、致用、正德、厚生」
在微博博友@沉默是金快乐是福 的帮助下,找到了 1915年出版的《科学》杂志的创刊号,其中的例言和发刊词中,分别提到这样两段文字:
「为学之道,求真、致用,两方面当同时并重」(图一)
「科学者,缕析以见理,会归以立例,有䚡理可寻,可应用以正德,利用厚生者也」(图二)
- 求真,就是探寻真理,真确的道理,探寻自然与宇宙的真确规律、万事万物的真确答案
- 致用,就是经世济民,学以致用,探索到的真理,规律,答案,不应该只停留在个人的「朝闻道、夕死可矣」的快乐上,还应该应用起来,改善人们的工作与生活
- 正德,就是启发民智,端正自我意识,让民众从宗教迷信中走出,从信息茧房中走出,能够明察秋毫,明辨是非,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,树立团结众人的大我精神,而非狭隘为己的小我私利
- 厚生,就是要造福百姓,改善民生,使国富民强。
本博将例言和发刊词截图贴出,供大家自行阅读和判断。本博需要额外指出这些内容中的一些非常值得注意的细节:
- 按例言中所介绍,1915年创刊《科学》杂志时,正是各国学界最近的创举,「文明之国,学必有会,会必有报,以发表期学术研究之进步与新理之发明,故各国学界期报实最近之学术发达史,而当世学者所赖以交通智识者也」,这显然与西方科技历史不相符。按现在的历史叙事,英国皇家学会早在创会的时候就有内部刊物了,Nature 更是早在 1869年就创刊了,到 1915年,这些刊物都有 50 - 200 年时间了
- 按例言中所列,物质科学与自然科学是互相分开的「今为编辑便利起见,略分次第如下:一通论,二物质科学及其应用,三自然科学及其应用,四历史传记,五杂俎,其余美术音乐之伦」,这与民国时期,甚至与西方科技历史叙事都不相符,因为物质科学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。另外,冠首的是通论,可见引贯物质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还有一套万物之道,这显然与西方科技叙事又不相同
- 发刊词中提到,杂志,这种形式的刊物在以前是文人墨客用来抒发郁闷,指点江山用的,这显然与西方历史叙事又不相同,最早在中国创办的所谓西方杂志,恰恰都是介绍科学知识和传教的
- 发刊词中提到,从蒸汽机发明到 1915年创刊此刊,时间不过百年,这显然也与当下的历史叙事不符。瓦特改良蒸汽机是 1765 年,1784年就投入商用了,到 1915年已经 150年了
- 发刊词中明确指出,宗教就是迷信,是禁锢人们思想的。「中世纪之初,欧洲大陆有宗教迷信,为人类智识进步之障碍….桎梏人心,莫此为甚」。这种论调显然不符合民国当时的环境,民国时期,孔教、基督教、天主教横行,即使现在的西方,也没有人敢说宗教是迷信,甚至按西方叙事,科技都是神父们开创的,是基督教孵化了科技…. 但是按我们的历史考察,中国古人所称的中世纪,开端就是 公元 429 年,即北魏建国开始,五胡乱华时期,那时中国不止有道教和佛教,还有祆教、拜火教、摩尼教等各种宗教迷信,比如安禄山的母亲,就是祆教女巫
- 发刊词中还提到,「机械之学,进而益精,蒸汽电力以为原动,则一日而有十年之获,一人而收百夫之用,近稽统计,远西名邦,若美若英若法若德,二十年间,国富之增,或以十倍、或以五倍、或以三倍」。但是按我们对西方经济历史的了解,西方在 1915年之前,其实从未有过如此快速的发展,不然也不会惊讶战后日本的重建速度,以及进入二十一世纪后,近20年来中国的发展速度了
- 发刊词中提到,伽利略是非科学家。「使非科学家,如加里雷倭 Galelio 者,本其好真之心,行其求是之志,血战肉薄,与宗教争此思想之自由」。而且伽利略并没有与宗教血战肉搏,只是被囚禁过,但这段描述倒是非常像是唐末时期的黄巢、朱温的事迹了。
- 发刊词中提到的不是文艺复兴,而是「文学复兴」。「文学复兴之后,人竞文彩,则赫胥黎、斯宾塞尔之徒,又主张以自然科学教育学子之道」。这里的文学复兴,不能不让人想起韩愈、柳宗元、杜牧等活跃在唐中末期的推崇先秦之风,针砭时弊的人物,而主张自然科学教育学子的人,又不能不让人想起王安石,在其文集中,就多次上书直言北宋当时教育的弊端,要遴选出能够变法之官吏并不容易,必须要改革教育。事实上,即使按现在的西方历史叙事,赫胥黎也从未提及过教育相关的事宜
- 发刊词中提到了科学与道德的关系,从中可以看出,古人理解的道德,实际上就是合乎天道的自我意识,启发民智,树立博大的情怀,并非简单的个人品德和狭隘的儒教礼法。「科学与道德,又有不可离之关系…. 人之为恶,固非必以是为乐也。辨理之心浅,而利害之见淆,有时敢为残贼而不顾。自科学之大昌,明习自然之律令,则是非之见真,而好恶之情得,人苟明於经济学之定理,知损人之於自损也,必不为以邻为壑之行;明於社会学之原理,知小已之不能犹存,而人生以相助为用也,而人偶共作慈祥,岂弟之心油然生矣。又况以科学上之发明,交通大开,世界和同,一发全身之感,倍切於畴。昔狭隘为已之私隐消於心曲,博施济众泽及走禽,恤伤救难,施於敌士,四海一家,永远和平,皆当於科学求之耳」